進化 - 達爾文以後// 信仰馬克思主義的西方科學大師古爾德(S.J. Gould)-- 方舟子
54 views
Skip to first unread message
丘延亮
Feb 13, 2009, 12:34:56 AM2/13/09
to y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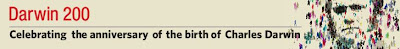
進化 - 達爾文以後
方舟子
《三思科學》電子雜誌
2005年第4期
方舟子,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生物化學博士,曾在美國羅切斯特(Rochester)大學生物系、索爾克(Salk)生物研究院做博士後研究,研究方向為分子遺傳學。1998年起主要從事寫作和網站建設。1994年曾創辦中文網絡文學刊物《新語絲》,主持新語絲網站,擔任新語絲社社長。2000年創辦中文學術打假網站「立此存照」,揭露了多起科學界、教育界、新聞界等領域的腐敗現象。目前擔任《中國青年報》、《經濟觀察報》、《長江商報》和《法制晚報》的專欄作者。著有《進化新解說》、《方舟在線》、《叩問生命——基因時代的爭論》、《進化新篇章》、《潰瘍——直面中國學術腐敗》、《長生的幻滅——衰老之謎》、《江山無限——方舟子歷史隨筆》、《餐桌上的基因》(再版改名《食品轉基因》)、《基因時代的恐慌與真相》、《尋找生命的邏輯——生物學觀念的發展》、《科學成就健康》、《批評中醫》、《方舟子破解世界之謎》、《方舟子帶你走近科學》、《你在吃補還是吃毒》等。一、躍變論、直生論和新拉馬克主義
1882 年,達爾文臨死前心滿意足地看到了他的兩個思想產兒之一——共同祖先學說已獲得了生物學界的公認,已難以找到生物學家還會懷疑進化的事實。但是他更心愛的另一個思想產兒——自然選擇學說卻遭遇不同的命運,只吸引了少數追隨者。它面臨的一些科學難題在當時沒有令人滿意的解答,而它的思想含義—— 那種機械的、看上去冷酷而消極的世界觀——也讓人在感情上排斥它。在達爾文死後,自然選擇學說越來越失去其吸引力,越來越多的生物學家採用其他機制來解釋進化是如何發生的。生物學家普遍排斥自然選擇學說的這個時期一直持續到20世紀40年代「現代綜合」學說統一了進化論與遺傳學為止,被「現代綜合」學說的創始人之一、托馬斯·赫胥黎的孫子朱利安·赫胥黎稱為「達爾文主義的日食」。
到1900年前後,自然選擇學說的聲譽跌到了低谷。大多數生物學家都支持別的學說,其中有三種學說被廣泛接受。其一是躍變論,認為新的形態和器官是源自大的躍變,而不是微小的變異在自然選擇的作用下緩慢而逐漸地累積下來的。包括赫胥黎在內的一些古生物學家由於強調生物化石的不連續性,而持這種觀點。在遺傳學誕生之後的一段時間內,遺傳學家們由於強調遺傳性狀的不連續性,也普遍接受躍變論。其二是直生論,認為在生物體有一種內在的「種系動力」在驅使生物朝著固定的方向進化,這種進化是非適應性的,與環境沒有關係,在某些情況下甚至能使物種因此滅絕。也有一些古生物學家持這種觀點。他們注意到某些動物化石的性狀,例如哺乳動物的牙齒和角的進化,似乎是呈直線性不斷增大的。他們認為,雖然牙齒和角最終會對生物體有用而變成一種適應性,但是在其進化初期,它們非常小,不可能有任何用處,因此它們的進化不可能是外在的自然選擇所驅動的,而是內在的動力使然,是一種促使牙齒或角不斷增大的動力驅使的結果。最終,這種動力會使牙齒和角大得變成累贅,失去了作用,甚至導致物種滅絕。例如,愛爾蘭麋鹿的角在內在動力的驅使下,變得越來越大,最終壓得無法抬頭,或容易與樹枝糾纏在一起,而導致愛爾蘭麋鹿的滅絕。古生物學家用來支持直生論的化石證據其實是一種假象。在只有少數化石標本時,很容易把它們用直線連接起來,而認為進化是直線式的,但是在有了更多的化石標本後,人們發現進化其實是分支式的。而且,那些被直生論者認為是一種累贅甚至導致物種滅絕的大型結構,也並非就沒有用途,例如愛爾蘭麋鹿的大角可能像現代麋鹿一樣是雄性用來相互角鬥爭奪配偶的,或是用於炫耀以吸引雌性,是性選擇的結果,而它們的滅絕發生於冰川紀結束時,是由於不能適應環境變化導致的。
愛爾蘭麋鹿
 當時信奉者最多的是第三種反選擇主義的學說——新拉馬克主義。拉馬克用用進廢退機制來解釋生物的進化,但是在其生前和死後相當一段時間,很少有人相信生物是進化來的,自然更少有人會去支持其進化機制。只有在達爾文確立了生物進化的事實之後,那些對自然選擇學說不滿意而尋找其他機制的生物學家,才重新發現了拉馬克提出的用進廢退機制,為了與拉馬克提出的其他顯然已經不合時宜的進化理論有所區別,它被稱為新拉馬克主義。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新拉馬克主義非常流行,甚至當時著名達爾文主義者斯賓塞、海格爾都認為只有把自然選擇學說和新拉馬克主義結合起來才能正確地解釋進化。
當時信奉者最多的是第三種反選擇主義的學說——新拉馬克主義。拉馬克用用進廢退機制來解釋生物的進化,但是在其生前和死後相當一段時間,很少有人相信生物是進化來的,自然更少有人會去支持其進化機制。只有在達爾文確立了生物進化的事實之後,那些對自然選擇學說不滿意而尋找其他機制的生物學家,才重新發現了拉馬克提出的用進廢退機制,為了與拉馬克提出的其他顯然已經不合時宜的進化理論有所區別,它被稱為新拉馬克主義。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新拉馬克主義非常流行,甚至當時著名達爾文主義者斯賓塞、海格爾都認為只有把自然選擇學說和新拉馬克主義結合起來才能正確地解釋進化。新拉馬克主義的核心是後天獲得的性狀能夠遺傳,也就是說,由於生物體的活動而出現的結構變化能夠傳給下一代,導致後代出現適應環境的進化。例如,拉馬克主義是這麼解釋斑馬為什麼能夠跑得那麼快的:因為古代的斑馬為了躲避捕食者的追捕,要不斷地跑,腿步肌肉因此受到鍛煉,變得越來越發達。發達肌肉的特性傳給了下一代,一代又一代傳下去,斑馬的腿部肌肉越來越發達,也就跑得越來越快。而穴居動物之所以沒有眼睛,是因為在黑暗的環境中眼睛對它們沒有用處,沒有得到使用,日益萎縮,最終消失。後天獲得性遺傳不僅包括這種用進廢退的情況,還包括任何由環境導致的適應性變化,例如生長在乾燥環境中的植物,會進化出保留水分的特徵。用進廢退和環境的作用都能使生物體的結構出現相應的變化,問題是這種變化能否傳給下一代?在達爾文時代,這不成問題,因為當時幾乎人人想當然地認為後天獲得性是能夠遺傳的,甚至達爾文也在其進化理論中給用進廢退保留了一席之地。只有在魏斯曼開始質疑、否認後天獲得性遺傳之後,新拉馬克主義者才面臨著用實驗證明自己的難題。
 產婆蟾
產婆蟾但是新拉馬克主義者能夠用來支持自己的實驗很少,他們反覆引用的實驗也可以有別的解釋。例如,法國生理學家布朗-塞奎(Charles EdouardBrown-Sequard,1817-1894)曾經做過一個實驗,損害豚鼠的大腦,則豚鼠的後代會出現癇癲。但是這並不足以證實癇癲就是遺傳而來,也有可能大腦的損傷產生了一種毒素,傳遞到子宮中而影響了胚胎的發育。遺傳學誕生後,新拉馬克主義者被逼入了絕境,更需要用實驗來證明自己。其中最熱衷於此的是奧地利生物學家卡姆梅勒(Paul Kammerer,1880-1926),他用兩棲動物做了許多實驗以證明環境能夠導致可遺傳的適應性變化。其中最著名的一個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做的產婆蟾實驗。產婆蟾是一種陸生的蟾蜍。水生的蟾蜍,雄的都有一個黑色指墊,交配時用於抓在雌蟾蜍身上免得滑倒,陸生的蟾蜍則沒有這個黑色指墊。卡姆梅勒強迫產婆蟾在水中生活,繁殖了幾代之後絕種了,但是在絕種之前,雄蟾蜍據稱長出了黑色指墊,而且一代比一代更明顯。卡姆梅勒聲稱水生的環境導致了「黑色指墊」這種適應性突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卡姆梅勒為了拉到資助,周遊列國到處演講。1923年,他帶著產婆蟾標本去英國演講,引起了轟動,也引起了遺傳學家貝特森的懷疑,要求檢查標本,遭到拒絕。有些生物學家試圖重複卡姆梅勒的實驗,都失敗了,因為產婆蟾極難養殖。1926年,在多方壓力下,卡姆梅勒終於允許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爬行類館長和維也納大學的一名教授檢查產婆蟾標本,他們發現所謂「黑色指墊」乃是用黑墨水塗上去的,向英國《自然》雜誌寫信揭露此事。此時卡姆梅勒正忙著往莫斯科寄運實驗設備和個人物品,準備到那裡擔任莫斯科大學的教授。一個多月後卡姆梅勒開槍自殺,留下一封給莫斯科科學院的遺書,在辭職的同時聲稱他是無辜的,是另外有人在他不知道的情況下造假。
在卡姆梅勒死時,新拉馬克主義在西方國家已接近破產,這個醜聞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但是新拉馬克主義在蘇聯卻正在興起。蘇聯政府邀請卡姆梅勒去蘇聯,就是想讓他領導對抗遺傳學的運動。卡姆梅勒的自殺使得這場運動被推遲了,直到1935年有了合適的人選——李森科。米丘林-李森科主義其實也是一種新拉馬克主義,這場政治鬧劇在壓制俄國生物學研究達30年之久之後,終於在1964年降下了帷幕。但是新拉馬克主義並沒有徹底退下舞台。雖然在當代生物學家當中幾乎無人相信新拉馬克主義,但是在生物學界之外,特別是在人文學界,新拉馬克主義仍然大有市場。這些當代新拉馬克主義者對達爾文主義的排斥不僅是出於對現代生物學的無知(拉馬克主義要比達爾文主義直觀得多,更容易被外行理解),而且更是出於一種思想感情:如果用進廢退能夠成立,那麼它表明生物並不是被動而緩慢地接受自然選擇,而是可以主動而快速地適應並改變世界。強調主觀能動性的新拉馬克主義要比達爾文主義積極得多,也溫暖得多,它給了人們美好的希望。但是美好的希望並不等於就是真理。
二、新達爾文主義
達爾文本人首先是個博物學家,他的學說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對生物變異和地理分佈的研究基礎上的。在達爾文主義日食時期,接受自然選擇學說的也主要是一部分追隨達爾文研究生物變異和地理分佈的博物學家。他們在野外親眼看到了生物對環境的奇妙適應性,這是無法用隨機的躍變或定向的直生說來解釋的。對許多適應性現象,既可以用用進廢退也可以用自然選擇學說來解釋。但是有某些適應性現象,則只有用自然選擇來解釋才顯得合理。早期的一個例子是在《物種起源》發表後不久,貝茨(Walter Bates)發現的昆蟲警戒擬態現象。昆蟲中常見的擬態現象是偽裝,例如枯葉蝶偽裝成枯葉、竹節蟲偽裝成樹枝,以避免被鳥發現。相反,那些味道難吃的昆蟲則盡量使自己翅膀的顏色鮮艷、耀眼,廣告自己的存在,以免被鳥誤食。貝茨在亞馬遜雨林研究蝴蝶翅膀的形態時,發現了一種新的擬態。他發現,在一個地方,不同種類的蝴蝶的翅膀圖案往往很相似,對鳥類來說,這些蝴蝶有的是不能吃的(例如透翅蝶),有的是可以吃的。貝茨認為,那些鳥類可以吃的蝴蝶通過模擬透翅蝶的警戒色,而保護了自己。由於蝴蝶並不能像控制肌肉那樣控制翅膀的顏色,因此像偽裝、警戒色以及警戒擬態的進化,就不可能是經由用進廢退而來的,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自然選擇:那些碰巧具有這樣的形態變異的昆蟲,較不容易被鳥捕食而能夠留下更多的後代。
 透翅蝶
透翅蝶在達爾文之前,博物學家並不關心一個物種內部的個體變異,把它們視為偏差。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學說強調個體變異的重要性,將之視為自然選擇的基礎,變異以及選擇作用成了研究進化論問題的博物學家們關注的核心問題。在19世紀後期,博物學家開始定量地研究變異及選擇作用。最早系統地定量統計生物性狀的是達爾文的表弟高爾頓(Francis Galton,1822-1911)。高爾頓同時也是「優生學」的創始人,這是由於他的錯誤的遺傳觀念。他不僅錯誤地認為人類一切特徵,特別是智力、品質、道德、創造力等等,都是能遺傳的,而且錯誤地認為人類遺傳受兩條「原理」的制約:一、祖先遺傳律:人的性狀各有一半來自父母,各有四分之一來自祖父母,依此類推;二、退化律:性狀顯著偏離平均值的父母生下的後代,該性狀將比其父母更接近於平均值。例如,假設有一群高個子的人互相通婚,數代之後他們的後代的身高將退化到人類的正常身高。高爾頓認為自然選擇無法改變這種退化趨勢,如果不加以人工干預,優良性狀將會逐漸喪失,人類的遺傳就是一代不如一代。為了將人類從災難的邊緣拯救下來,高爾頓從動植物育種得到啟發,提出了兩套方案(這兩套方案被其追隨者稱為「積極優生」和「消極優生」),一方面,「上等人」只能跟「上等人」結婚,並且要盡可能多地生孩子,另一方面,高爾頓呼籲政府插手,勸阻或防止「下等人」生殖。為了證明他的主張,他做了許多統計。比如,他統計了從1660年到1865年間286位著名的英國法官,發現九分之一有父子或兄弟關係。於是他得出結論說,當法官的能力是遺傳的,這些法官天生就繼承了當法官必備的品質。顯然,高爾頓犯了統計上的兩大錯誤,一是取樣不隨機,二是完全無視其他因素的影響(例如家庭環境對職業取向的影響、裙帶關係對陞遷的影響等等)。他用同樣的方法證明了科學家、詩人、政治家、將軍甚至划船手等等全都是遺傳的。
在高爾頓的影響下,一些生物學家也採用統計方法研究動物群體,但是目的卻是為了證明自然選擇的作用。威爾登(Raphael Weldon,1860-1906)測量不同地區的蝦的各種性狀,發現它們呈正態分佈,並測量蝦的器官,研究其相關性。許多人認為這項研究奠定了生物統計學的基礎。威爾登的好友、數學家皮爾森(Karl Pearson,1857-1936)不僅發明了許多統計分析方法,而且從理論上證明即使高爾頓的「遺傳原理」能夠成立,自然選擇也會對動物群體產生持久的影響。維爾登通過多項野外研究證明了這一點。例如,他統計了螃蟹身體大小與死亡率的相關性,發現在沉積物較多的水中,體型較大的螃蟹要比較小的螃蟹更容易存活,在經過許多代以後,累積下來的選擇作用將使螃蟹群體發生永久性的變化,使其平均體積變大。
威爾登和皮爾森都是堅定的達爾文主義者,以後也成了孟德爾主義的頑固反對者。不過,在達爾文主義日食這個時期最堅定、最著名的達爾文主義者是德國生物學家魏斯曼(August Weismann, 1834-1914)。在1883年發表的《論遺傳》一書中,魏斯曼認為自然選擇是進化的唯一機制,不僅反對躍變論、直生論,也否認用進廢退以及一切後天獲得性的遺傳。這種強硬的態度,顯然與達爾文本人既強調自然選擇的重要性,又不否認用進廢退的作用的靈活態度不同,因此達爾文的學生羅曼斯(George J. Romanes)認為這背離了達爾文本人的主張,而將之稱為新達爾文主義,也即排除獲得性遺傳的達爾文主義。魏斯曼原先是個實驗動物學家,研究昆蟲的變形和水螅的性細胞。由於視力出了問題,不適於做顯微鏡觀察,逐漸改而從事理論研究。但是早期對水螅性細胞的觀察已使他認識到在動物性細胞中,包含著某種特殊的遺傳物質,必需被仔細地保存,並一代代傳下去。他把這種遺傳物質稱為種質,而身體結構(體質)是根據來自上一代種質提供的信息建造的,並且是用來攜帶種質,進而傳給下一代的。種質與體質是隔離的,在體質發生的變化無法傳給種質,是不能遺傳的,生物體只能傳遞種質。
魏斯曼的種質學說在理論上否認了拉馬克主義。由於用進廢退而導致的身體變化不能影響到種質,因此就是無法遺傳的,被用來證明用進廢退機制的進化現象,例如退化器官,可以解釋為是由於自然選擇壓力的鬆弛導致的。魏斯曼並且試圖用實驗來否證拉馬克主義。在著名的切老鼠尾巴實驗中,他連續切除了22代老鼠的尾巴,測量各代老鼠尾巴的長度,發現老鼠後代的尾巴並沒有因此而變短。拉馬克主義者抗議說這個實驗並無說服力,因為他們所說的獲得性遺傳是對自然環境的適應,而不是人為的損傷。拉馬克主義者在這麼為自己辯護的時候,卻忘了他們拿來證明獲得性遺傳的那些實驗中,有的正是要證明人為的損傷也是能夠遺傳的(例如布朗-塞奎的豚鼠癇癲實驗)。魏斯曼的實驗至少證明了發生在身體組織的損傷不會影響到種質。魏斯曼同時也首先嘗試用實驗來顯示自然選擇的作用。例如,他把各種顏色的毛毛蟲放在各種顏色的背景中,統計鳥類、蜥蜴的捕食結果。
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學說是建立在生物群體中具有多種變異的基礎之上的,但是達爾文一直對變異的來源感到困惑。他認為它們可能是環境的作用、生物體的用進廢退導致的。魏斯曼既然徹底否認獲得性能夠遺傳,就必須為變異尋找新的來源。他認為這個來源就是有性生殖。魏斯曼認為種質的基本單位是定子(相當於後來說的基因),在有性生殖過程中,來自父母雙方的定子混合起來,出現了新的遺傳組合。這種遺傳重組,提供了幾乎是無限的變異可能性。這樣,魏斯曼就正確地認識到,有性生殖導致的遺傳重組是變異的主要來源,這也是有性生殖的意義。但是,這個過程只能是重組已有的變異,全新的變異是如何出現的?魏斯曼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卻沒能給出令人滿意的解釋。他認為新變異是由於定子的變化引起的,但是他否認這種變化是隨機產生的,而是環境的直接影響或種質內部營養因素差異直接導致,並且在種質內部經歷了適者生存的過程,他稱之為「種質選擇」。魏斯曼顯然沒有意識到,他的「種質選擇」學說雖然有選擇之名,卻承認環境的誘導作用,已經背離了自然選擇學說。魏斯曼犯下的這個錯誤,是因為他把新拉馬克主義者所做的一個實驗結果信以為真。新拉馬克主義者聲稱,在把蝴蝶的蛹進行冷或熱處理之後,不僅羽化而出的蝴蝶的翅膀色彩發生了變化,而且其未經處理的後代的翅膀色彩也發生了變化。
魏斯曼是比達爾文本人還要堅定、徹底的達爾文主義者,終其一生一直在為捍衛達爾文主義而戰。在其晚年,新拉馬克主義已經沒落,他需要面對的是一種新興的躍變論——突變論。
三、突變論
生物性狀的變異有兩類,一類是連續變異,例如人的身高,它的數據分佈是連續的,在高矮兩個極端中間有無數只有細微差異的變異,沒有明顯的分界線。另一類是不連續變異,例如孟德爾所研究的豌豆種子形狀,一種是圓形的,一種是皺形的,界限分明。那麼,哪一種變異是生物進化的源泉呢?以威爾登和皮爾森為代表的生物統計學派認為連續變異是重要的,而不連續變異是沒有意義的異常現象。當時在英國,以貝特森(William Bateson)為代表的遺傳學家則持相反的觀點,認為不連續變異要比生物統計學家所願意承認的普遍得多,也比連續變異重要得多,進化是跳躍的方式進行的。這兩個學派爭論極為激烈,乃至導致威爾登和貝特森由同事好友變成仇敵。
孟德爾從研究豌豆的不連續變異入手,發現了遺傳定律,其論文在 1900年被重新發現,貝特森很快將其譯成英文,並成為英國孟德爾主義的領袖人物。根據孟德爾遺傳定律,生物遺傳是穩定的,不受環境直接的影響,而且是顆粒性,遺傳物質不互相融合。這不僅否定了拉馬克主義,也否定了傳統的融合遺傳觀念,從而解決了達爾文主義面臨的如何避免優勢性狀因為融合而被稀釋的問題。孟德爾遺傳定律正是自然選擇學說所需要的遺傳理論。但是,由於當時遺傳學家和生物統計學家之間的激烈衝突,使雙方都看不到這一點,錯過了將孟德爾遺傳定律與自然選擇學說相結合的機會。生物統計學家排斥孟德爾定律,認為大多數性狀是連續的,不在孟德爾定律的解釋範疇內;而遺傳學家則認為大多數性狀都是不連續的,能夠用孟德爾定律解釋其遺傳。
 月見草
月見草孟德爾定律的重新發現者、荷蘭植物學家德弗裡斯(Hugo de Vries,1848-1935)在研究月見草時,發現它們偶爾會突然地出現新的類型,他把這種現象稱為「突變」(我們現在知道,這些新類型並非基因突變導致的,而是染色體重排的結果)。「突變」的結果使花的形態出現重大變化,重大到像是不同的物種。在德弗裡斯看來,新物種的形成並非像達爾文主義者所設想的那樣是在自然選擇的作用下緩慢地累積微小變異的結果,而是通過一次突變突然形成的,「沒有任何可覺察的預備,也沒有任何過渡階段」。他在 1901-1903年陸續出版的《突變論》一書中,系統地闡述了這個新的進化學說。德弗裡斯認為自己並不是完全否定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學說,而是對它進行了修正:自然選擇不是對個體變異發揮作用,而是在更高的層次上發揮作用,是在突變產生新種後,決定它們是否能夠生存下去還是被淘汰掉。
丹麥遺傳學家約翰森(Wilhelm Ludwig Johannsen,1857-1927)所做的純係菜豆實驗似乎為突變論提供了證據。菜豆豆粒有的大,有的小,如果總是讓大豆粒植株自交,小豆粒自交,這樣持續選擇下去,是否會讓大豆粒植株的豆粒越來越大,小豆粒植株的豆粒越來越小呢?他讓菜豆自花授粉,這樣持續若干代後,獲得了一大一小兩個純係菜豆,它們無法做進一步的選擇,豆粒大小保持穩定。純係菜豆的大小雖然仍會出現變異,但是這種變異是環境因素導致的,不能遺傳,對這些變異進行選擇不會有效。因此約翰森認為自然選擇只能對已有的遺傳差異進行挑選,而一旦獲得了純係,自然選擇就不再起作用,因此只有通過突變,才能使菜豆的性狀出現真正的改變,而創造出新種。
摩爾根實驗室在研究果蠅時,發現了大量的突變,並且通過對突變的研究,證明了基因位於染色體上。這樣,就證實了魏斯曼的種質學說,從而徹底否定了後天獲得性能夠遺傳。基因突變被視為是產生新性狀的唯一源泉,進化中的變化都是由於出現新的突變導致的。突變壓力驅使生物體朝著某個特定的方向突變以系統地產生新的性狀。因此,進化的動力不是自然選擇,而是突變壓力,自然選擇對生物進化是無關緊要的,最多不過是消極地淘汰有害的突變。這種非適應性的突變壓力的觀念讓人聯想到了直生論所說的內在動力。突變論在否定後天獲得性遺傳的同時,也否定了自然選擇的威力,在其主張者看來,達爾文主義和拉馬克主義一樣,都成了過時的學說。
四、群體遺傳學
在以威爾登和皮爾森為代表的生物統計學派和以貝特森為代表的孟德爾主義學派激戰正酣的時候,曾有人試圖當和事佬。早在1902年,皮爾森的好友、英國統計學家猶勒(George Udny Yule, 1871-1951)發表論文指出,孟德爾遺傳定律和生物統計學派所測量的連續變異並不是不相容的。由於這句話,猶勒在後來被許多人視為群體遺傳學的先驅,並對生物統計學派和孟德爾主義學派聽不進去猶勒的真知灼見而深表惋惜。事實上,仔細閱讀猶勒的論文可以發現,猶勒試圖調和孟德爾定律與連續變異的解決方案與後來的群體遺傳學並無相同之處,甚至是背道而馳的。群體遺傳學以孟德爾定律為基礎,把連續變異當成孟德爾定律的特例(多基因遺傳),而猶勒恰恰相反,把高爾頓的祖先遺傳律做了修改後當成基礎,而把孟德爾定律視為特例。猶勒的做法,理所當然地兩面不討好,被生物統計學派和孟德爾主義學派所共同拒絕。
此後的十幾年間,遺傳學的研究表明孟德爾主義者把遺傳規律設想得過於簡單了。1909年,瑞士遺傳學家尼爾森-厄勒(Herman Nilsson-Ehle, 1873-1949)在研究小麥種子顏色的遺傳時,發現紅色種子與白色種子的比例是63:1,而不是孟德爾定律所預測的3:1;而且紅色種子的顏色深淺不盡相同,有的較深,有的較淺。他推斷必定有3對基因依照孟德爾定律同時控制著小麥種子顏色的遺傳,才會出現這種情況。他進而指出,如果某個性狀是由10對基因控制的話,就會出現近6萬種不同的表現型,而由於這些表現型的差異很小,就會形成連續變異。差不多同時,美國遺傳學家伊斯特(Edward Murray East, 1879-1938)和愛默森(Rollins Adams Emerson, 1873-1947)在研究玉米性狀的遺傳時,也有了類似的發現。越來越多的遺傳學家意識到,連續變異也是可以用孟德爾定律來解釋的,只不過涉及到了多對基因。另一方面,遺傳實驗也表明,基因突變極少導致生物形態出現重大變化,而且這種大突變幾乎都是有害的。更常見的突變是溫和而細微的突變,只能使性狀出現細小的變異。如果沒有自然選擇的作用的話,這些細小的變異就難以累積下來、傳播開去。由於這些發現,到20世紀10年代後期,摩爾根等遺傳學家逐漸放棄突變輪,改而接受自然選擇學說。但是他們對自然選擇學說的理解相當簡單:在有益的突變逐漸擴散到群體中去的同時,有害的、甚至中性的突變一旦出現,就會很快被淘汰。這種簡單化的觀點被稱為選擇的「經典假說」。
將基因學說和自然選擇學說真正結合起來的,是群體遺傳學的三位創建者,英國的費歇(Ronald Fisher, 1890-1962)、荷爾登(J.B.S. Haldane, 1892-1964)和美國的萊特(Sewall Wright, 1889-1988)。這三個巨人的專業背景各不相同。費歇在大學讀的是數學和物理專業,1912年劍橋大學獲得數學學士學位,其畢業論文研究的是天文學的測量問題。但是他對生物學的興趣由來已久,在中學畢業時獲得一套達爾文全集做為畢業禮物,後來與達爾文的兒子萊奧納德‧達爾文(Leonard Darwin,1850-1943)結成忘年交。他力圖把遺傳學與達爾文進化論結合起來,而他在大學時期所受到的物理訓練,又激勵著他去尋找像物理定律那樣簡單明瞭而又定量化的生物定律。在畢業前夕發表的題為《孟德爾主義與生物統計學》演說中,費歇已設想二者終將會結合在一起。畢業後,費歇做過保險公司統計員、中學數學教師等工作,業餘從事學術研究。在他擔任中學校長期間,完成了一篇論文證明孟德爾定律能夠用於解釋生物統計學派對連續變異的研究成果。此時英國孟德爾主義學派和生物統計學派還在惡鬥,這篇調和派論文被倫敦王家學會所拒,1918年發表在愛丁堡王家學會的會刊上。之後,費歇先後到羅森斯坦研究站、倫敦大學學院、劍橋大學從事專業研究,致力於從數學上證明孟德爾遺傳定律不僅不與自然選擇學說相衝突,而且正是達爾文進化論所需要的遺傳理論。他的這些研究成果,於1930年彙集成《自然選擇的遺傳理論》一書出版。荷爾登的父親是一名著名的生理學家,他從小就幫助其父親做生理學實驗,之後在牛津大學接受人文學教育,但是最終以科學研究做為職業,其研究生涯始於1922年到劍橋大學研究生物化學,1933年轉到倫敦大學學院擔任遺傳學教授。荷爾登多才多藝,是罕見的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在生物化學、遺傳學、生理學、進化論、生命起源、醫學、數學等眾多領域都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並熱衷於科學普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他在1924年發表了其第一篇研究群體遺傳學的論文,在1932年出版群體遺傳學的經典著作《進化的因素》(在該書中他寫道:「我能夠以權威身份論述自然選擇,因為我是最懂得其數學理論的三個人當中的一個。」)。萊特與另兩人不同,他是生物學科班出身,1912年去哈佛大學拜卡斯特(William E. Castle, 1867-1962)為師研究哺乳動物的遺傳,其博士論文有一個簡明易懂的題目——《對豚鼠毛色及其他皮毛性狀的遺傳的細緻研究》。這篇論文使他在 1915年畢業後很容易就獲得了美國農業部的一份工作,因為美國農業部自1906年以來就在研究豚鼠的近親繁殖,正需要有人來分析這些數據,用以指導如何改良牲畜。在為美國農業部工作期間,萊特研究出了一種統計方法(通徑係數法)用以分析近親繁殖的效果(萊特自己喜歡指出,他本人就是近親繁殖的產物,其父母是表兄妹),這個方法後來被廣泛應用於行為遺傳學、社會學和經濟學的研究。1926年萊特前往芝加哥大學擔任遺傳學教授時,他已經系統地研究了群體遺傳學問題,形成了一系列獨特的看法,例如他的長篇經典論文《孟德爾群體中的進化》實際上在1925年已經完成,但是遲至1931年才發表。群體遺傳學是萊特的生命,他的研究工作一直持續到生命的最後一年。
 豚鼠
豚鼠這三個人通過創建群體遺傳學,為現代進化論奠定了數學基礎。群體遺傳學把生物的進化定義為一個群體內部基因頻率的改變。如果某個基因突變能使生物體具有生存優勢,即使這個優勢非常細小,在自然選擇的作用下,也會逐漸累積下來,只要有足夠長的時間,就會逐漸擴散到整個群體,而如果知道了這個優勢的大小(適宜度),那麼就可以定量地計算出該基因頻率的增長速度。但是自然選擇並不像摩爾根認定的那樣必然會淘汰有害的基因突變,如果有害基因是隱性的話,那麼自然選擇只會降低其頻率,卻不會消滅它。特別是,如果雜合體(在一對等位基因中一個正常一個有害)比純合體(兩個等位基因都是正常或有害)更有生存優勢的話,那麼自然選擇將會讓兩個等位基因的比例保持平衡狀態。而且,基因突變是按一定的速率隨機出現的,即使這些突變沒有優勢,也會以低頻率持續在群體中出現、流通。在環境變化時,這些原來沒有優勢的突變有可能變得具有優勢,而被自然選擇所利用。這樣,保持遺傳多樣性就有利於一個群體長期的生存。
但是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三位創建者卻有不同的、甚至針鋒相對的看法,特別是在費歇和萊特之間,長期存在激烈的爭論。費歇受物理學的影響,把自然選擇定律視為像氣體定律那樣精確的定律,在為自然選擇學說建構數學模型時,做了一些簡單化的、抽像的假設。他認定只有在一個大群體中才會出現有意義的進化,如果一個群體過小的話,不具有足夠多的遺傳變異,很容易滅絕。而在一個大群體中,從長遠來看,隨機因素顯得不重要,只有自然選擇才是生物進化的決定性因素。費歇假定新的基因突變對性狀的影響一般來說是很細小的,屬於一個物種的正常變異,在自然選擇的作用下,優勢基因突變才會緩慢地增加其頻率。他只研究自然選擇對單個基因的影響,而不考慮不同基因之間的相互作用,這種做法被其批評者貶稱為「豆袋遺傳學」,因為在以前遺傳學教科書中,習慣用不同顏色的豆子代表不同的等位基因,一個基因組就像是一袋互不相干的豆子的集合。「豆袋遺傳學」並不像其批評者所指責的那麼簡陋。如果一個群體非常大,而每個基因的作用都很小,隨機分佈在整個群體中,那麼各基因就可看成或多或少是獨立的。相反地,萊特通過動物育種意識到,在小群體中,不同的基因之間往往能夠出現複雜的相互作用,特別是近親繁殖能夠產生在大群體中不容易見到的基因組合,而這些新的變異有可能被隨機地保留、固定下來,也就是所謂遺傳漂變。在萊特看來,在自然環境下,一個大群體也能被分隔成一些局部小群體,在這些小群體中,遺傳漂變會產生新的基因組合。自然選擇進而發揮作用,決定這些新組合的命運,從而出現比費歇所設想的要快得多的進化。萊特對小群體中遺傳漂變的重視,使他被稱為「遺傳漂變先生」。荷爾登的立場大致處於費歇和萊特之間。荷爾登所建立的數學模型與費歇的相似,針對的是大群體和單個基因的變化。但是荷爾登認為自然選擇對單個基因的作用過程並非總是很緩慢的,有時能比費歇所提出的快得多。他用實例說明了這一點,最著名的一個例子是英國樺尺蛾的工業黑化現象。在19世紀中葉之前採集到的這種蛾的翅膀都是淺灰色的。1848年,昆蟲學家首次在工業城市曼徹斯特附近採集到了黑色翅膀的樺尺蛾標本。荷爾登假定這時候黑蛾的比例只有1%,而經過53代後,到了1901年,黑蛾比例則幾乎達到100%。荷爾登計算出,這個進化過程要能發生,平均每一代黑蛾和灰斑蛾後代的生存比例必須高達1.5,這種選擇強度是費歇理論難以想像的。在後來,荷爾登也認為基因之間的相互作用能夠是很重要的,獨立提出了一些與萊特非常類似的觀點。不過,荷爾登認為大多數群體在大部分時間內是不分隔成小群體的,因此從長遠來看,遺傳漂變的作用是很有限的。遺傳漂變對生物進化的作用究竟有多大,直到今天仍然是個有爭議的問題。
五、現代綜合
進入20世紀30年代,群體遺傳學的三位創建者雖然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有爭議,但已一起從理論上證明了達爾文主義和孟德爾主義不僅不互相衝突,而且相輔相成。那些在野外做觀察研究的生物統計學家所獲得的進化數據,都可以從遺傳學原理推導出來。在孟德爾遺傳學的基礎上,自然選擇可以完滿地解釋生物的適應性進化,不需要拉馬克主義、直生論、突變論等其他學說。這些理論研究涉及到複雜的數學計算,不是一般的生物學家們所能理解的。而且只有理論沒有實驗和野外觀察的驗證,也很難被生物學家們所接受。因此,他們的研究工作,對當時的生物學界並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群體遺傳學的創建者關心的是一個群體內部的演變,並不考慮更高層次的進化,特別是物種生成的問題,只有荷爾登在其經典著作中有過簡略的討論,提及隔絕群體是物種生成和大進化的關鍵,但是在當時研究物種生成問題的主要是博物學家、系統分類學家和古生物學家,而他們對群體遺傳學還幾乎一無所知。只有把群體遺傳學的成果應用於實驗和野外觀察,解決物種生成的問題,綜合生物學各個領域的成果,才能完成自然選擇學說和基因學說的統一,讓自然選擇學說和共同祖先學說一樣成為生物學的理論基礎。在20世紀30、40年代,眾多生物學家為完成這個目標添磚加瓦,代表人物是四個美國生物學家——遺傳學家杜布贊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 1900-1975)、動物學家邁爾(Ernst Mayr, 1904-)、古生物學家辛普森(George Gaylord Simpson, 1902-1984)和植物學家斯特賓斯(George Ledyard Stebbins Jr., 1906-2000),其中,又以杜布贊斯基的影響最大。
 杜布贊斯基
杜布贊斯基杜布贊斯基出生於俄國並在俄國受的教育。在20世紀20年代,俄國遺傳學家契特維裡科夫(Sergei S. Chetverikov, 1880-1959)獨立地發現了群體遺傳學的一些原理,並且強調理論與實驗的結合。他和費歇一樣,相信在自然群體中存在著眾多隱性基因,但是和費歇不同的是,他用從美國購買來的果蠅做遺傳實驗證明了這一點,這是首次用實驗證明在自然群體中存在著廣泛的變異。契特維裡科夫還是一個傑出的教師,影響了許多俄國生物學家,包括在俄國研究瓢蟲的杜布贊斯基。可惜的是,在李森科主義興起後,契特維裡科夫學派就被消滅了。幸運的是,在此之前,1927年,杜布贊斯基移民美國,把契特維裡科夫學派的影響帶到了西方。杜布贊斯基到美國後最初跟隨摩爾根研究果蠅遺傳學,此後果蠅一直是他的實驗材料。但是,杜布贊斯基在俄國接受的博物學訓練使他在從事遺傳學研究時有一個獨特的視角,他強調實驗室裡的發現必須在野外獲得證實,從而成為彌合理論、實驗室實驗和野外觀察的鴻溝的最佳人選。1937年,杜布贊斯基發表了《遺傳學和物種起源》。在這部繼《物種起源》之後最為重要的進化論論著中,杜布贊斯基介紹了群體遺傳學家所做的數學研究,特別是萊特的研究,總結實驗遺傳學家對遺傳突變的研究成果,並證明在實驗室裡通過人工突變產生的變異在自然群體中也存在,而且自然群體有足夠的可遺傳的變異為自然選擇提供原料。這樣,杜布贊斯基就在理論上、實驗上和觀察上綜合了自然選擇學說和孟德爾遺傳學,對實驗生物學家和野外生物學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刺激了各個領域的生物學家都投身到進化論的研究當中來。

遺傳學和物種起源
接下去的十年,是達爾文主義碩果纍纍的十年。杜布贊斯基與萊特合作,繼續研究自然群體的遺傳。有趣的是,在此之前,在《遺傳學和物種起源》初版中,杜布贊斯基認為自然群體中的大部分變異是中性的、非適應性的,是遺傳漂變產生的。但是在與「遺傳漂變先生」的合作研究之後,杜布贊斯基反而更加強調自然選擇的作用。他發現許多以前被認為是漂變導致的中性變異,很顯然具有適應性,是自然選擇的結果,從而證明群體遺傳學的創建者已提出來的「平衡假說」:自然選擇不僅能夠導致群體的進化,而且也能保持遺傳多樣性。杜布贊斯基也觸及了被群體遺傳學創建者所忽略的物種問題,認為物種是由群體組成的生殖共同體,不同的物種之間存在「隔離機制」(例如地理、行為或生理差異)使它們無法雜交。杜布贊斯基並指出,同一物種的不同群體之間的地理變異,特別是地理隔絕,是導致它們進化成不同物種的必要條件。邁爾發展了杜布贊斯基的這些觀點,把達爾文主義應用於分類學研究,提出一個至今仍被廣泛接受的物種定義(所謂物種的生物學概念:「物種是一群實際上或有可能相互交配的自然群體,它們與其他這樣的群體存在生殖隔絕。」),並提出了在地理變異和隔絕條件下新種產生的模型,認為重大的進化幾乎總是發生在隔絕的群體之中。他在1942年出版的《系統分類學與物種起源》是現代進化論的經典著作。如果說群體遺傳學創建者解決了顆粒遺傳與連續變異的矛盾的話,那麼杜布贊斯基和邁爾則解決了連續變異與分立(不連續)的物種的矛盾。比物種產生更高層次的進化,即生物的不同類群之間的大進化,又是如何呢?古生物化石記錄了大進化的證據。辛普森在1944年出版《進化的步調與模式》,將達爾文主義推廣到古生物學。他所做的定量分析表明,達爾文主義能夠很好地被用於解釋化石記錄,古生物的大進化可以被視為是微進化的累積結果,而且是像達爾文主義所預測的那樣不具有方向性。杜布贊斯基、邁爾、辛普森都只研究動物的進化,斯特賓斯則指出植物的進化同樣能被達爾文主義所解釋(代表作為1950年出版的《植物的變異與進化》一書)。
20世紀40年代,現代進化論已經被成功地應用於生物學的所有領域。1942年,朱利安‧赫胥黎發表《進化:現代綜合》一書,綜合了達爾文主義在各個領域的研究成果,現代達爾文主義也因此被稱為「現代綜合學說」。標誌著這個偉大的綜合過程的最終完成的,是1947年在普林斯頓成立了「遺傳學、分類學和古生物學的共同問題委員會」。組成這個委員會的三十個學術權威代表著生物學的不同領域,但有著一個共同的觀點:自然選擇是一切適應性進化的機制。1959 年生物學界紀念《物種起源》發表100週年,同時也在慶祝自然選擇學說的全面勝利。
六、基因選擇學說
現代綜合進化論為進化生物學的研究搭起了一個基本框架。在20世紀50年代之後的所謂後綜合時期,進化生物學的理論研究向兩個方向演變,一方面是「硬化」現代綜合進化論,進一步擴大自然選擇的適用範圍,強調生物進化的適應性和漸變性,形成選擇主義或適應主義流派,被其對手貶稱為極端達爾文主義,更中性的說法也許該稱為強達爾文主義;另一方面則是質疑自然選擇的適用範圍和功效,與強達爾文主義針鋒相對,強調生物進化的非適應性、偶然性、定向性和躍變性,提出種種所謂非達爾文主義學說。
 螞蟻
螞蟻強達爾文主義集中研究的主要問題是,複雜的動物行為是如何進化而來的?特別是,動物的利他行為是如何誕生的?有一些利他行為是所謂「互惠利他」(reciprocal altruism),即甲幫助乙,並預料乙在以後會回報甲。這種行為對自己有利,嚴格地說不是真正的利他行為,用自然選擇解釋其起源毫無困難。但是有一些社會行為則明顯是利他的,特別是社會性昆蟲的無私行為,該如何解釋?在達爾文研究自然選擇理論時,就對工蟻的利他行為感到不可思議。它們放棄了繁殖能力,卻一心一意為別的螞蟻服務,這似乎是與自然選擇相違背的,因為自然選擇是一個完全自私的過程,是以個體的繁殖優勢來衡量的,那些繁殖能力差的個體的後代將逐漸被淘汰,更不要說根本就不能繁殖的個體了。如何解決自私的自然選擇和利他的社會行為的矛盾?達爾文注意到,一個蟻巢中所有的個體都是最直接的親屬,不是父母與子女關係,就是兄弟姐妹關係,因此一個蟻巢可以視為一個巨型的個體,其成員的分工合作就像一個個體的不同器官組織分工合作一樣,工蟻放棄了生殖能力為別的螞蟻服務就像胃放棄了生殖能力為別的器官服務一樣,沒什麼可奇怪的。不過,在達爾文之後到現代綜合完成這段時間內,利他行為的問題基本上被忽略了,在群體遺傳學的創建者中,只有荷爾登研究過這個問題,指出幫助近親的利他行為有助於近親們所共享的利他基因的生存與傳播。
在後綜合時期,一場有關「集體選擇」的爭論使利他行為又成為熱點。自然選擇歷來被認為是對個體所做的選擇。但是在1962年,英國動物學家維因-愛德華茲(Vero Copner Wynne-Edwards, 1906-1997)認為自然選擇也可以對集體進行選擇,「集體選擇」學說可以很容易地解釋動物的利他行為,它們是為了集體(特別是物種)的利益而犧牲了個體利益。但是許多進化生物學家懷疑集體選擇是否能夠發生。他們堅持達爾文的觀點,認為自然選擇只是對個體而不是群體做出選擇。如果個體只是為了集體而犧牲自己和後代的利益,就會被集體中的自私自利者坐享其成,這種純粹利他的個體的後代要麼也變成自私自利者,要麼就被淘汰,因此利他行為為自然選擇所不容。抨擊集體選擇學說最有力的是美國生物學家威廉斯(George C. Williams, 1926-),他在1966年出版的《適應性與自然選擇》一書給了「集體選擇」學說致命的一擊。威廉斯進而指出,基因才是自然選擇的真正目標,自然選擇是經由基因之間的競爭而實現的。這個「基因選擇」學說後來被英國動物學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1941-)形象地稱為「自私的基因」,成功地進行了普及而廣為人知。

自私的基因
基因選擇學說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它能夠很好地解釋利他行為。英國生物學家漢密爾頓(W.D.Hamilton, 1936-2000)把達爾文、荷爾登對利他行為的解釋加以改進,提出了「親屬選擇」的概念:一個個體能夠通過幫助親屬的繁殖而影響自然選擇的結果。親屬選擇概念被成功地應用於破解社會性昆蟲的利他行為之謎。螞蟻等社會性的昆蟲有一套獨特的遺傳系統:受精卵發育成雌蟻(新蟻後和工蟻),未受精的卵則發育成雄蟻。因此雌蟻的基因組一半來自蟻後,一半來自蟻王,而雄蟻只有來自蟻後的那一半,基因組是雌蟻的一半。在遺傳學上,雄蟻屬單倍體,雌蟻屬雙倍體。蟻王當然也是單倍體,它的精子不必象卵子那樣要經過減數分裂(即把二倍體變成單倍體)丟掉一半基因,而是把全部的基因都傳給了雌蟻。因此,對於雌蟻來說,她們的基因來自蟻後的那一半最可能有二分之一相同,但是來自蟻王的那一半則是完全相同的,姐妹們彼此之間的遺傳關係不是像人那樣只有二分之一,而是四分之三。如果她們生兒育女,與兒女的遺傳關係不過二分之一,還不如姐妹們親。這樣,對於工蟻來說,與其生兒育女,不如一心一意照顧蟻後讓她生產更多的姐妹,那樣更有利於保存自己基因。
在用自然選擇學說解釋動物行為時,英國生物學家梅納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 1920-2004)提出的「進化穩定策略」是另一個與「集體選擇」針鋒相對的重要概念。為了爭奪資源(比如食物、配偶),一個物種的成員彼此之間要進行爭鬥。在這種爭鬥中,那些能凶狠地攻擊、殺死對手的個體似乎更有生存優勢,但是為什麼同一物種的成員之間的爭鬥經常只是一種裝模作樣的儀式,靠虛張聲勢就決出了勝負,而不是你死我活的?在集體選擇學說看來,這是因為用儀式爭鬥法解決衝突可以避免傷害,對物種的繁衍有好處。但是梅納德‧史密斯給出了一個更為精緻的答案。做為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假定個體在搏鬥時,只採用兩種極端的戰術:「鷹派」不顧一切地搏鬥下去,直到一方受重傷或死亡而失去搏鬥能力為止;「鴿派」或者只是虛張聲勢地嚇唬一番,一旦搏鬥真正開始,就逃之夭夭。很顯然,一個完全由鴿派組成的群體不可能是穩定的。因為如果突變出了一隻鷹派,在與鴿派搏鬥時戰無不勝,有生存優勢,它的鷹派後代也會越來越多。但是,一個全部由鷹派組成的群體不可能是穩定的。因為如果突變出了一隻鴿派,雖然它在搏鬥中每戰必敗,但是也不會有傷亡,而鷹派彼此之間的爭鬥會有傷亡,這樣,在一個由鷹派組成的群體中,做為鴿派有生存優勢,它的基因就會在後代中傳播開去,鴿派在後代中會越來越多。只有鷹派和鴿派各佔一定的比例,這個群體才達到了進化穩定策略狀態。這樣,通過分析動物爭鬥行為,梅納德‧史密斯開創了一個新領域—— 進化博弈論,自然選擇是博弈的決策者。
七、社會生物學
1975 年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O. Wilson, 1929-)出版《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標誌著一門新的學科——社會生物學的誕生。威爾遜將「社會生物學」定義為系統地研究所有社會行為的生物學基礎,在書中總結了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將達爾文主義與動物行為學綜合起來。在最後一章,他將動物行為學的研究成果推廣開去,試圖將進化論也用於解釋人類的行為,把心理學和社會學也和進化論綜合起來。恰恰是這一章,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激烈的爭議,引發了自《物種起源》出版以來最為激烈的一場進化論大辯論。在威爾遜看來,人類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就像其他動物的社會行為一樣,是由基因決定的,是自然選擇的結果。儘管其本意不過是試圖為人類行為的起源提供一個進化論的解釋,而不是宣揚什麼政治主張,但是這種有遺傳決定論嫌疑的主張讓人聯想起了20世紀初期「優生學」運動的悲劇和納粹的罪惡。因此,在人權活動家看來,威爾遜是種族主義者、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又因為威爾遜認為男女的行為差別由遺傳決定,因此在女權活動家看來,威爾遜是性歧視主義者。右翼保守分子也同樣不放過威爾遜,因為他居然認為進化論可以解釋宗教、道德的起源。威爾遜有一度如過街老鼠,在各地做學術報告時經常遭遇抗議示威,甚至遭到襲擊:他在美國科學促進會的年會上做完報告後,一個聽講者朝他潑了一臉冷水。連他的同事好友、遺傳學家列萬廷(Richard Lewontin, 1929-)也與他反目成仇。他們兩個人曾在芝加哥大學一起將群體遺傳學結合進生態學。威爾遜搬到哈佛大學後,也請列萬廷搬了過去。為了抗議越南戰爭,列萬廷放棄了美國科學院院士的頭銜,成立「科學屬於人民」、「生物學辯證法組織」,反對任何形式的打著科學旗號的反動勢力。在列萬廷看來,威爾遜已與反動派為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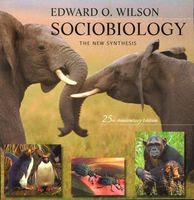 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
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面對著來自左右兩方面的攻擊,威爾遜能夠用來支持自己的觀點的證據很少。其中最強有力的,是有關人類亂倫禁忌的研究。對人類亂倫禁忌的起源,歷來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和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 1908-)認為亂倫禁忌是文化現象。弗洛伊德相信,人類普遍存在戀父、戀母情結,亂倫禁忌做為一種強加的道德觀念抑制在家庭成員中自然產生的性慾望。與弗洛伊德同時的芬蘭社會學家威斯特馬克(Edward Westermarck, 1862-1939)的觀點恰好相反,把亂倫禁忌當成遺傳現象。他認為其起因是因為熟悉消滅了性慾望,也就是說,兒童發育時期的親密關係(母子之間,同胞之間)導致性吸引力的消失。威斯特馬克認為,這是自然選擇的結果,因為亂倫後代得隱性遺傳病的機率大大增加,具有生存劣勢。也就是說,生物學的原理是支持這種解釋的。以後的研究證實了威斯特馬克的觀點,亂倫禁忌的確是遺傳決定的。這些證據來自三個方面:一、社會生物學的研究表明,所有的靈長類動物都存在亂倫禁忌,那麼人類做為靈長類的一員,似乎也應該有這樣的本能。這種現象,最早於五十年代在日本的一個動物園觀察到。那裡飼養的日本獼猴存在著社會等級制度,最高等級的雄猴與任何一頭雌猴頻繁交配,卻避開了它的母親。以後這種現象在所有的靈長類中都被觀察到,包括最為淫蕩的矮小種黑猩猩。在許多靈長類,為避免近親繁殖,青春期的成員將加入別的群體,而那些呆在一起的同胞,一般也避免彼此交配。二、跨文化的人類學研究表明,所有的人類社會,不管多麼野蠻,也都存在亂倫禁忌,也就是說,這很可能是與文化無關的一種本能。也許有人會舉出反例:古埃及、印加和夏威夷的王室要求王室的同胞通婚。但是這只是王室的特例,可以認為是為了保證王權不旁落而採取的違反自然天性的舉動。三、社會學的調查也支持熟悉消滅了性慾望的說法。在以色列的集體農莊,成員的兒女被混在一起集體撫養。調查表明,那些在同一組裡一起長大的小孩,特別是那些在三到七歲之間一起長大的小孩,彼此之間雖然感情深厚,卻不存在性的吸引力。近年來,斯坦福大學的人類學家阿瑟‧沃爾夫(Arthur P. Wolf)調查了台灣14400名婦女的婚姻史。這類婚姻都是包辦婚姻,但是分為兩類:一類是童養媳,一類由媒人撮合,在結婚當天男女雙方才見面。結果也支持預測,前者的離婚率更高,生育率更低,表明小時候一起生活的確破壞了性吸引力和婚姻幸福。
威爾遜開創的這個研究領域,雖然仍不乏爭議,卻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承認。近十幾年來,行為遺傳學和神經生物學的研究已提供了大量的證據,足以證明至少人的某些行為,是受遺傳因素影響的。遺傳因素必定是長期進化而來,那麼,用進化論解釋人的本能行為的由來,就成了一個可以成立的課題。社會生物學中針對人類行為的這部分內容因此獨立出來,形成一門被稱為進化心理學的新學科。但是,這門學科從它誕生之日起,就已先天不足。它既不可能在人類進化史上找到任何心理「化石」做為直接證據,也不會被允許以人為材料進行進化實驗,因此注定了它不可能像進化生物學一樣成為真正的科學,而必定像它所希望取代的社會科學一樣在科學與非科學甚至偽科學之間徘徊。由於缺乏直接的證據,進化心理學的研究只能依賴從間接的證據得出推論。這些間接的證據來自四個方面:生物學的原理(一種行為有無生物學上的優、劣勢,自然選擇能否因此起作用),跨文化的研究(如果一種人類行為在不同文化中都存在,就可能是先天的),與其他動物特別是靈長類動物的社會行為的比較(如果一種社會行為在其他動物中也存在,那麼可能是一種本能),以及在人類社會中做的調查。顯然,一個進化心理學的結論能否令人信服,取決於這些證據是否確鑿。對亂倫禁忌的研究成果被認為是進化心理學的一個勝利,但是進化心理學的結論很少像亂倫禁忌這樣有強有力的證據,而且不涉及敏感的社會問題。畢竟,把亂倫禁忌視為本能,不會冒犯任何人。當觸及敏感的社會問題時,就可能遭遇強烈的批評,而如果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持自己,那是咎由自取。2000年,美國生物學家蘭迪‧桑希爾(Randy Thornhill)和人類學家帕爾默(Craig T. Palmer)合出一本書《強姦的自然史》,聲稱強姦是一種自然行為,是男人的本能,是男人用於傳播基因的一種生殖策略,理所當然地引起了眾怒。他們能用於支持自己的觀點的證據都經不起推敲,連許多進化心理學家也認為是一個恥辱。
八、間斷平衡
生物的進化可以分成三個層次:物種內部的微小變化即所謂「微進化」、新種生成和產生物種以上的新類群(新屬、新科等等)的所謂「大進化」。現代達爾文主義將生物的進化定義為群體內基因頻率的改變,這種改變不僅產生了微進化,也導致了新種的產生和大進化,也就是說,新種產生和大進化並沒有特別的進化機制,而是微進化緩慢累積的結果。但是這種漸變觀似乎與化石記錄並不吻合,化石記錄表明,新種、新類群往往是突然出現的。現代達爾文主義對此的解釋與達爾文當初的解釋相同,歸結為化石記錄不完全,是過渡型物種沒有能遺留下化石而導致的假像。20世紀30-40年代,現代達爾文主義興起後,在20世紀初風靡一時的躍變論沒有了市場,只有個別的人在抵抗這個潮流,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德裔美國遺傳學家高茲史密特(Richard Goldschmidt, 1878-1958)。他在1940年提出微進化的結果不能推廣到物種形成和大進化,每一個新種的產生、每一次大進化都來源於一次躍變——一次對生物發育有重大影響的大突變產生了一些「有希望的怪物」,再由這些有希望的怪物產生新的物種、新的類群。高茲史密特的觀點很自然地飽受非議,因為在當時遺傳學家們已經知道,對生物形態有重大影響的大突變的結果幾乎總是災難性的,使生物無法存活,出現的怪物更可能是「無希望」的。
到了20世紀70年代,躍變論又開始以新的面目出現。一些古生物學家覺得總把新物種化石的突然出現歸結為記錄的不完全難以令人信服,他們認為新形態的突然出現未必都是假像,有可能是真實存在的。1972年,兩名美國古生物學家埃爾德裡吉(Niles Eldredge, 1943-)和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1941-2002)聯合提出「間斷平衡」學說,認為從化石記錄看,生物的進化有這樣的模式:長時間的只有微小變化的穩定或平衡,被短時間內發生的大變化所打斷,也就是說,長期的微進化之後出現快速的大進化,漸變式的微進化與躍變式的大進化交替出現。在間斷平衡學說的支持者們看來,大進化有著與微進化不同的機制,而這種大進化機制,不是自然選擇,而是其他因素導致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發育制約」:胚胎發育的模式——藍圖——一旦建立起來,就有了一種內在的連貫性,難以通過突變逐漸加以改變,生物體將沿著固定的途徑發育、生長,使物種長期保持穩定,新的遺傳變異由於不能與已有的發育模式相容,因此不可能出現或保留下來。只有在特殊的情況下,發育制約被解除了,胚胎發育沿著新的途徑進行下去,使得生物體形態出現重大的變化。間斷平衡學說的支持者們很明智地避免把躍變的原因歸結為大突變,而是歸結為調控基因發生的突變,這類基因的突變即使非常微小,也能夠對發育過程產生重大影響,使生物形態出現大的變化。但是,並不是所有的這些改變都是可行的,已有的發育模式也制約了發生變化的可能性,限定了生物體只能沿著為數不多的新途徑進化。換句話說,新性狀的產生並非是隨機的,而是有一定的方向性,這些方向是被發育藍圖決定了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歷史偶然性」,例如創立者效應(一小群個體偶然離開群體到別的地方開闢領地,在基因漂變的作用下,本來稀少的基因可能會急劇增多,本來頻率高的基因反而變得很低或丟失)或瓶頸效應(一個群體受到災難性打擊,只有少數個體存活了下來,基因頻率因此發生改變),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新性狀並非自然選擇的結果,未必具有適應性。
間斷平衡的倡導者是以反對強達爾文主義的面目出現的,他們並不否認漸變和自然選擇的重要性,但是他們強調躍變在大進化中的重要性,在解釋伴隨著大進化出現的多樣性時,他們更強調它的非適應性、歷史偶然性和發育制約。他們對自然選擇機制的看法也與強達爾文主義者不同,認為自然選擇不僅僅對基因或個體起作用,也能在更高的層次上(群體、物種)進行選擇,對基因或個體的選擇出現了微進化,對群體的選擇出現新物種,而對物種的選擇則出現了大進化。但是,生物進化的速率是難以測定的,那些被用於支持間斷平衡的化石證據,也能夠被用於支持漸變論。在某個層面上看來是穩定的現象,在另一個層面上看卻可能是不斷變化著的,只不過沒能在化石中體現出來。例如,中生代哺乳動物化石的形態變化看上去並不大,但是在這個時期,哺乳動物在生理方面的進化(例如胎生、哺乳、體溫調節等等)一定是非常重大的,只不過無法從化石中覺察出來。因此,平衡有可能只是假像。另一方面,間斷式的躍變也有可能是假像。道金斯曾經舉過一個假想的例子,一個鼠群在經過6萬年緩慢得難以覺察的進化後,其身體可以變成像大象那麼大,但是6萬年在地質上只是一瞬間,是不可能分辨出來的,因此原本極其緩慢的微進化在化石上就會表現出快速的大進化。
 櫻草 Primula
verticillata
櫻草 Primula
verticillata
即使間斷平衡是真實存在的進化模式,也與現代達爾文主義並不矛盾。達爾文主義並不認為進化的速率必定是均勻的,群體的結構(大小、遺傳變異程度、分佈等等)、發育制約、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出現的不同選擇方向和壓力等因素都能影響進化的速率,出現不同的進化模式。物種出現長期的穩定並不是不可思議的事,例如穩定性選擇能夠消滅那些偏離常態的個體,減少變異,使得群體在穩定的環境中保持相同的性狀。現代達爾文主義也不否認在特殊的情況下,生物能發生躍變式的進化。在許多植物中,異源多倍體化(雜交之後,染色體數目倍增)被公認為能導致「瞬間」生成新種,例如兩種櫻草Primula verticillata和P. Floribunda的雜交。這兩種櫻草各有9對18條染色體,它們的雜交後代一般地也有18條染色體,但是因為其中的一半各來自兩種櫻草,沒法配成9 對,所以是不育的。然而,有少數雜交後代的染色體數多了一倍,成了36條,因此就可以配成18對,這樣的雜交後代可以自行繁殖,並無法再跟其父母本交配,是一個新的物種。類似這樣的多倍體化很可能是被子植物產生新物種的最主要方式,在進化史上,可能有超過半數的單子葉植物是多倍體化的產物。除了這種特殊的躍變,漸變的速率也可能很快。萊特早就提出,一個群體如果被分成數個區域性同類群,進化速率會快得多,而另一位現代達爾文主義的創建者邁爾最早強調因創立者效應和瓶頸效應導致的小群體對產生新種的重要性,在這種情況下,進化的速率會是非常快的。災難性事件和其他獨特的歷史事件對生物進化的重大影響也早就被認識到,只不過其不可預測性使得人們難以對它們做定量的研究。總之,雖然大進化的機制是否等同於微進化的機制,是一個仍有爭議的問題,但是,間斷平衡學說與現代達爾文主義的分歧,實際上要比其倡導者要人們相信的小得多。
九、分子進化
當達爾文創建進化論時,人們對遺傳的機制還一無所知。而當現代達爾文主義的創建者們歡呼達爾文主義與經典遺傳學成功地結合在一起時,人們對遺傳的化學本質和分子機制同樣一無所知。現代達爾文主義創建於分子生物學誕生的前夜。1944年艾菲力(Oswald T. Avery, 1877-1955)證明DNA是遺傳物質,1953年沃森(James Watson, 1928-)和克裡克(Francis Crick, 1916-2004)提出DNA的雙螺旋結構模型,生物學從此進入了分子時代。正如經典遺傳學草創之初,有許多人認為達爾文主義已被推翻一樣,在分子生物學剛剛興起時,同樣有人預言達爾文主義將會成為歷史。事實恰恰相反,分子生物學的研究基本上支持達爾文主義的主要結論。分子生物學揭示了生物界在分子水平上的一致性,在所有的生物體中遺傳密碼以及基本的分子機制都是相同的,證明了進化論關於「所有的生物由同一祖先進化而來」的命題。假基因等所謂「垃圾 DNA」的發現表明生物體內存在「分子化石」,這是生物進化的一條極其重要的證據。分子遺傳學的「中心法則」表明遺傳信息是單向的,只能從核酸傳向蛋白質,而不能從蛋白質傳回核酸,從而從根本上否定後天獲得性遺傳的可能性,否證了達爾文主義在歷史上的主要對手拉馬克主義。同時,分子生物學為研究生物進化的過程和機理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在以前,生物學家們只能通過古生物化石的研究和現存生物的形態結構比較確定各物種親緣關係的親疏,從而繪出種系發生樹;現在,我們已完全可以在分子水平上,通過比較蛋白質的氨基酸序列和基因的核甘酸序列,不僅在總體上肯定了傳統生物學的結果,而且使種系發生樹的描繪更精確,達到了定量化的程度。
分子生物學的發展在使進化論的研究更加精確的同時,也發現了新的問題。在以前,對遺傳變異存在兩種觀點,摩爾根、繆勒(Hermann J. Muller,1890-1967)的「經典假說」認為大多數基因座上的等位基因都是「野生型」的,突變型基因多是有害的,自然選擇會使突變型基因只以很低的頻率存在。而現代達爾文主義的「平衡假說」則認為自然選擇也能保持遺傳多樣性,如果雜合體具有優勢,就會使得大多數基因座會有多種等位基因。杜布贊斯基等人通過研究果蠅的變異,發現其遺傳多樣性更符合「平衡假說」的預測。但是在分子生物學誕生之前,對遺傳變異的研究只限於對形態變異的觀察,無法精確地知道有多少基因的參與才導致了所觀察到的形態變異,而對那些不顯著的微小變異則根本無法觀察到。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人們開始用電泳技術研究蛋白質的變異。1966年,杜布贊斯基的學生列萬廷與哈比(John L. Hubby, 1932-1996)合作,為了驗證「平衡假說」,用這個方法首次對群體中的遺傳變異程度做了定量的估計,發現要比以前認為的高得多,在一個果蠅群體中,大約30%的基因座是多態的(有不同的等位基因)。以後的研究發現,一般生物的遺傳多態性都是10-20%。如此高的遺傳多態性與「經典假說」相矛盾,但是卻同時對「平衡假說」也提出了挑戰。由此出現了「中性學說」學派,認為蛋白質存在如此高的多樣性,表明在分子水平上,生物進化受自然選擇的作用很小,而是按一定的速率隨機地突變。一個蛋白質的變異能夠被保存下來,不是因為它有生存優勢,而是因為它對生存沒有太大的害處,也就是說,它是好的、不好不壞或只有輕微的壞處,都有同等的機會被保留下來(壞處太大了當然就被自然選擇淘汰了),誰能保留下來是中性漂變的結果。

木村資生
中性學說是日本遺傳學家木村資生(Motoo Kimura,1924-1994)在1968年提出來的。除了蛋白質的變異數太高外,中性學說還有其它的依據。20世紀60年代以後,分子生物學家開始能夠測定蛋白質的氨基酸序列,他們通過比較不同物種的同一種蛋白質的氨基酸序列的異同,推算出蛋白質的突變速率大概是每年10^-9個氨基酸。這個數目看上去很低,但是木村資生認為,如果蛋白質的進化是受自然選擇的作用的話,這個數目則顯得太高了。荷爾登曾經提出了一個「選擇的代價」的模型,認為自然選擇會給生物體帶來代價,導致死亡或絕後,因此自然選擇不能太強,速度不能太快,否則會引起生物群體內個體數目的銳減,最終導致滅絕。他根據這個模型估算了一下,得出自然選擇速度的上限是大約每三百代發生一次基因改變。木村指出,對於哺乳動物而言,蛋白質的突變率大概等於每兩三年基因組就要發生一次改變,遠遠高於荷爾登給出的上限,因此蛋白質的進化不可能是由自然選擇導致的,只能是中性漂變的結果。中性學說的第三個依據是,儘管不同的蛋白質的進化速率有快有慢,它們似乎都有一個固定不變的進化速率(所謂「分子鍾」)。在他看來這不可能是自然選擇的結果,因為環境的變化速率不可能是固定不變的。最後一個依據是,一個蛋白質的不同部分有不同的進化速率。蛋白質的不同部分的重要性不同,比如酶的活性區就要比邊沿區重要。研究表明,蛋白質的重要區域的進化速率要比別的區域慢。木村資生認為,如果自然選擇對蛋白質進化起作用的話,一個區域越重要,選擇的壓力就越大,它的進化速率就應該越快才對。而如果分子進化是中性漂變導致的的話,一個區域越重要,可能的中性突變就越少,進化的速率理所當然就顯得慢。
木村資生提出了分子進化的中性學說,在進化生物學界掀起了軒然大波。反對中性學說、相信自然選擇對分子進化起決定性作用的所謂選擇主義者對中性進化的依據一一做出了反駁。針對木村在荷爾登的模型基礎上認為蛋白質突變率過高的說法,選擇主義者反駁說,荷爾登的模型只適用於那類導致群體規模減少的「硬性」選擇,但是自然選擇也可以是軟性的,並不一定導致群體規模的減少。對於軟性選擇來說,選擇的速度不受限制。由於自然選擇在實際上可軟可硬,難以給它定一個上限,我們也就不清楚蛋白質的進化速率對自然選擇而言是不是太高了。選擇主義者進一步指出,木村計算得出每兩三年基因組就改變一次時,是假定每個基因都是獨立受自然選擇作用的;但是,實際上不同的基因往往連鎖在一起,同時接受自然選擇的挑選。如果考慮到這種情況,蛋白質的進化速率實際上並不像木村認為的那麼高。同樣,木村經過計算,認為基因多態性若是自然選擇保留優勢雜合基因的結果,則10-20%的多態性高得離譜。但是他的計算也是假定了每個基因都是獨立的。如果考慮到一次自然選擇能夠同時對一個以上的基因起作用,這個數目也就不算那麼高。有的選擇主義者更指出,如果基因多態性純屬中性漂變所致的話,它應該比我們已知的高得多。
木村用中性漂變解釋分子鍾現象,也遭到了選擇主義者的質疑。木村認為,中性漂變是一個隨機的過程,隨機的過程在長時間來看變化總是很穩定的,而自然選擇不可能產生穩定的變化,因為自然選擇與環境的變化相關,環境在長時間來看很難有持續穩定的變化。生物形態的變化無疑是自然選擇作用的結果,它們就不像分子鍾那樣有固定的速率。那麼分子鍾是以代還是以年為單位呢?根據中性學說,進化的速率等於中性漂移的速率,也就是正比於基因突變的速率。基因突變是在細胞分裂時DNA複製發生了錯誤而產生的,因此基因突變的速率應該正比於細胞分裂的次數,也就是正比於代數。因此,中性學說預言分子鍾應該以代為單位,那些每一代時間較短的生物的分子鍾要比每一代時間長的跑得快。可惜,比較結果表明,蛋白質的分子鍾是以絕對時間,而不是以代為單位的,每代時間短的生物的分子鍾跑得跟每代時間長的一樣快。這是不符合中性學說的預測的,相反的,卻可以用自然選擇來解釋。舉個例子來說,老鼠大概每四個月一代,大象大概每三十年一代,它們都受到細菌的選擇。四個月後,細菌積存了四月的變化,就對老鼠選擇一次,而對大象要每三十年才選擇一次。但是在三十年後,感染大象的細菌與感染老鼠的細菌相比,積存了一百倍的變化,因而對大象的選擇強度也就是對老鼠的一百倍,其結果是,儘管老鼠和大象的代數不同,進化速率卻是一樣的。這是個過於簡單的例子,但是卻說明自然選擇要比中性漂變更好地解釋為什麼蛋白質分子鍾以絕對時間為單位。
 老鼠和大象有著同樣的進化速率
老鼠和大象有著同樣的進化速率木村的最後一個依據是蛋白質不同區域的進化速率不一樣,重要的區域進化速率慢,而不重要的區域進化速率快。他認為,這種現象最好用中性漂變來解釋。不重要的區域要比重要的區域可以有更多的不好不壞的中性突變,所以那裡的進化速率就會比較快。但是選擇主義者指出,這個現象同樣可以用自然選擇來解釋。用收音機的選台來打個比方,蛋白質的重要區域就像是粗調旋鈕,選定了就不好亂動,以免跑台,但是不重要的區域卻像是微調旋鈕,可以不停地轉動直到選准了台。所以,在選擇主義者看來,蛋白質不重要區域的進化並非毫無意義的中性漂變,而是在慢慢地以微弱的優勢逼近最佳的結果。這兩種說法孰是孰非呢?因為我們不知道一種蛋白質是否可以有很多種完全相同的突變,也不知道非重要區的那些被保留下來的突變是對蛋白質功能毫無影響還是有微弱優勢,所以我們不知道究竟誰的理由更站得住腳。
木村是根據蛋白質序列提出中性學說的,20世紀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DNA序列被測定,中性主義和選擇主義之爭的戰場從蛋白質轉到了DNA。 DNA的進化速率和蛋白質的進化速率並不相同,我們已經知道蛋白質的分子鍾是以絕對時間為單位的,但是DNA的分子鍾卻是以代為單位的,即每代時間較短的生物,其DNA分子鍾要比每代時間長的跑得快,這是符合中性學說的預測的。絕大部分DNA序列是不具有功能的(例如不編碼氨基酸的內含子、假基因等所謂「垃圾DNA」),而那些編碼氨基酸序列的DNA序列中,有一些位點即使發生了改變也不會影響氨基酸序列。序列分析表明,一般來說,那些不編碼氨基酸或不影響氨基酸序列的DNA序列(簡稱非功能區)的多態性,要高於那些編碼或決定氨基酸序列的DNA序列(簡稱功能區)的多態性。由於DNA功能區決定著生物的性狀,這就表明它們受到了自然選擇的作用,是自然選擇減低了功能區序列的變異程度。換句話說,DNA非功能區的變異程度是由中性漂變決定的,而自然選擇則對功能區發揮作用。
總之,自然選擇無疑能夠影響並保持分子多態性,但是中性漂變也是導致某些多態性的重要因素。有關中性學說的正確性和適用範圍目前仍然沒有定論。不過現在大多數生物學家都認為,中性學說能夠更好地解釋DNA特別是非功能區DNA的進化,而功能區DNA和蛋白質的進化則還要受到自然選擇的作用。
十、進化發育生物學
早在19世紀,胚胎學家就已經開始在思考動物胚胎發育與進化的關係。德國胚胎學家拉特克(Martin H. Rathke, 1793-1860)在19世紀20年代發現在鳥類和哺乳類的胚胎的早期都出現了鰓裂,它們在胚胎發育時似乎經過了魚的階段。這個發現看來很符合「事物大鏈條」(自然界階梯)的觀念:如果胚胎發育是一個從不完美到完美的過程,那麼,較完美的動物(鳥類、哺乳類)在胚胎發育時就必然出現較不完美的動物(魚類)的形態。在此基礎上,德國麥克爾(J. F. Meckel, 1781-1833)和法國賽利(Etienne Serres, 1787-1868)歸納出了一條後來被稱為「麥克爾-賽利定律」的法則:高等動物的胚胎在發育過程中,基本上逐步經過類似低等動物的階段。這聽上去有點像進化論,其實是目的論的:胚胎如此發育,是由於它們有某種追求完美的內在傾向,使得它們跟自然界階梯相平行。實驗胚胎學的創始人馮‧貝爾既反對進化論,也反對自然界存在從低到高的階梯,認為各種動物都按一定數目的原型分門別類。在他看來,胚胎發育是一個從簡單到複雜,從同質到異質,從普遍到特殊的過程。在胚胎發育的早期,各種生物胚胎都比較簡單、同質,所以才出現了相似的形態。這個後來被稱為「馮‧貝爾定律」的胚胎發育法則,也完全是目的論的。他也無法解釋,為什麼鰓裂就是同質的、普遍的?
達爾文最早指出,動物的胚胎發育,是反對神創論的最有力的證據:如果生物是神創的,他應該讓受精卵以最直接的方式發育成成體,何必讓整個胚胎發育過程如此迂迴曲折?為什麼陸棲的脊椎動物的胚胎發育要經過鰓弓階段?為什麼須鯨的胚胎有牙齒?為什麼高等脊椎動物的胚胎有脊索?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這些奇怪的形態是它們的祖先的遺產。為什麼這些遺產在胚胎發育中會保留下來呢?達爾文認為,這是因為導致進化的變異一般是在胚胎發育的晚期才發生的,對早期胚胎幾乎沒有影響,這一方面增加了成體和胚胎的差異,另一方面又使得不同類群的動物的早期胚胎保留它們的共同祖先的形態,非常的相似:「因此,胚胎結構相同透露了祖先相同。」他並預言:對不同種類的胚胎進行比較,應當能夠找出共同祖先的線索。
不同動物早期胚胎的相似,意味著它們有共同的祖先
達爾文曾經抱怨說,他在《物種起源》中所提出的這些胚胎學的證據,沒有引起注意。不過這種情形很快就改變了。在《物種起源》發表後不到十年,海克爾不僅大力鼓吹達爾文的說法,並把它推向了極端:動物的胚胎發育是在遺傳和適應規律的制約之下,簡化和壓縮了的進化過程的重演。如果這條「重演律」是正確的,那麼,通過研究胚胎發育,就能夠弄清楚動物的進化過程。在重演律提出之後的三、四十年間,激發了研究者極大的興趣,促進了胚胎學研究的繁榮,使得胚胎比較成為確定生物同源關係的重要工具,並做出了許多重大的發現。
但是進入二十世紀之後,雖然胚胎比較仍然被視為生物進化的重要證據,動物在胚胎發育時的確保留著某些祖先的特徵,但是極端的重演律卻逐漸被拋棄了。一個原因是重演律有太多的例外,胚胎發育對進化過程的重演並不那麼忠實。另一個原因是找不出一個有說服力的理由說明胚胎為什麼要重演祖先特徵——歷史上存在過的,並不等於就應該被保留下來,特別是那些歷史特徵並無用處,比如,哺乳動物的胚胎並不用鰓裂呼吸。因此,後來的胚胎學家傾向於接受馮‧貝爾定律,簡單地把胚胎發育視為從簡單到複雜的過程。但是,在上面我已說過,馮‧貝爾定律無法解釋鰓裂和其他的重演特徵。
胚胎學的研究雖然提供了許多有關胚胎發育的知識,但是都是描述性的,沒法回答有關胚胎發育的最根本的一些問題:是什麼樣的因子導致胚胎發育過程中發生的變化?這些變化是如何遺傳下去並進化的?從1930年代起,高茲史密特等人試圖用遺傳學的方法回答這些問題,從而創建了發育遺傳學,但是進展極其緩慢。直到1980年代,由於分子遺傳學方法被應用於研究胚胎發育,發育生物學才發生了一場革命。近20年來的研究使我們從分子水平上對胚胎發育有了一定的瞭解,也使得我們可以重新評價、解釋重演律。
發育遺傳學的研究表明,生物的胚胎發育,是一個基因調控的過程,不同的基因依次被打開、關閉。由於這是一個信號一級一級地放大的過程,越早表達的基因,其後來的影響將會被越放越大。因此,達爾文的解釋是對的:能夠保留的突變一般發生在胚胎發育的晚期,因為如果突變發生在發育的早期,將會對後面的發育過程發生重大的影響,其結果往往是災難性的。這樣,那些較早表達的基因,往往是在進化史上較為古老的祖先基因,較晚表達的基因,則是後來逐漸加入的。既然胚胎發育過程,是一個從祖先基因到新近基因的依次表達的過程,那麼,重演進化過程的某些特徵,也就並不奇怪了。
 魚鰭通過進化變成四肢
魚鰭通過進化變成四肢在最早表達的基因中,有一種屬於同源異形基因的Hox基因,它是動物形態藍圖的設計師,在發育過程中控制身體各部分形成的位置。如果同源異形基因發生突變,會使得動物某一部位的器官變成其他部位的器官,叫做同源異形。比如,讓某個同源異形基因發生突變,能使果蠅的身體到處長眼睛,在該長眼睛的地方長出翅膀,或者在該長觸角的地方長出了腳。Hox基因在所有的脊椎動物和絕大部分無脊椎動物中都存在,調控的機理也相似,這表明它可能是最古老的基因之一,在最早的動物祖先中就已存在。Hox的突變一開始時在胚胎早期引起的變化不大,但隨著組織、器官的分化定型,突變的影響逐步被放大,導致身體結構發生重大的改變。這可以用來解釋所謂「寒武紀物種大爆發」。寒武紀開始於5.7億年前,結束於5.1億年前,是地質年代古生代的第一個紀。寒武紀之前的地層的動物化石較少,而在寒武紀的地層中,發現了種類繁多的動物化石,有的古生物學家甚至認為動物各門的祖先在這個時期都已出現,稱為「寒武紀物種大爆發」。為什麼會發生「寒武紀物種大爆發」,長期以來被視為一個謎,有多種解釋,現在有了一個較令人信服的解釋:那時候基因結構、發育過程都較簡單,Hox的基因突變容易被保留,結果導致了身體結構的多姿多彩。除了 Hox 基因,還有其他一些在發育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的調控基因在不同類群的動物中都存在著。在分子水平上,所有的動物都有著非常相似的基本發育機制。
發育生物學的這些重大發現,甚至使我們可以在實驗室中模擬生物的大進化現象。比如,把斑馬魚的Hox基因的表達速度變慢,結果發現在胚胎發育時,魚鰭細胞層層堆積變成了骨頭,最後又長出了趾頭。這可以使我們瞭解魚鰭是怎麼進化成四肢的。又比如,Tbx4 和Tbx5 是控制前肢(翅膀)和後肢的分化的基因,Tbx4 只在後肢細胞中表達,Tbx5 只在前肢細胞中表達。在雞的胚胎發育時讓這兩種基因的表達掉換,讓Tbx5 在後肢部位表達,讓Tbx4在前肢部位表達,結果發現雞翅膀變成了雞腿,而雞腿變成了雞翅膀。從這些研究中我們也可以知道,胚胎發育時的調控基因的微小突變可以導致成體的巨大變化,生物新類型的產生可能是在生物胚胎發育過程中基因突變的結果。
一個生物體既是在發育過程中它的基因相互作用以及基因與環境的相互作用的產物,也是一個歷史進化過程中突變與自然選擇的產物。通過分析發育過程中的基因表達、突變和選擇,不僅可以瞭解生物發育的過程和機制,知道一個生物體是如何形成的;而且可以揭示生物進化的歷史和機制,知道一個物種是如何起源的。可以預見,隨著發育生物學的發展,越來越多的進化難題,特別是大進化難題,將被解決。一門統一了進化生物學與發育生物學的新學科——進化發育生物學已經誕生,並成為當代生物學中最活躍的研究領域之一。
*****
附:
信仰馬克思主義的西方科學大師
方舟子
南方週末
2002年10月10日第974期
今年5月,美國當代最著名的進化生物學家斯蒂芬。古爾德(S.J. Gould)因患癌症病逝,享年60歲。他在學術上的最大成就是和埃爾德裡吉(N.Eldredge)共同提出「間斷平衡」學說,認為生物的進化模式是一個舊物種在長時間的穩定後,在短時間內出現新物種。
政治信仰被小心遮掩著
古爾德同時還是一位優秀的作家,近30年來為美國《博物學》雜誌撰寫了300篇普及進化論的專欄文章,這些文章陸續結集出版後,都成了暢銷書。他還是批判神創論和抨擊遺傳決定論的活躍鬥士,頻頻出現在媒體上。這一切使得他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公眾人物,其知名度絕不在卡爾。薩根之下,去年美國國會圖書館曾將他稱為美國「活著的傳奇人物」。許多美國生物學家聲稱,他們是因為小時候讀了古爾德的文章才對生物學發生興趣的。
近年來國內雖然已引進翻譯了不少古爾德的著作,其名氣卻遠不如薩根。而國內在介紹古爾德時,也無人提及———或者根本就無人知道 ———古爾德是個馬克思主義者。在美國也很少有人知道這一點。古爾德的政治信仰被宣傳他的人小心翼翼地遮掩著,例如《科學》雜誌刊登的死者略傳中,僅以「古爾德的政治觀點一直屬於左派,而他的哲學最能以世俗人本主義概括」一句話模模糊糊地帶過,以致有位讀者去函提醒,不該忽視古爾德的馬克思主義信仰,他的科學工作和科學著作都顯示了他的政治背景和思想的影響。
在膝蓋上學會馬克思主義
古爾德的信仰屬於家傳,他的父母都是紐約的左派,他曾經聲稱他「在父親膝蓋上學會了馬克思主義」,不過後來又說他的政治觀點和父親存在分歧,這大概指的是他不接受斯大林主義。古爾德一直熱衷於政治活動,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多次參加反戰、反種族主義示威,特別是在1969年,哈佛大學學生為抗議校方捲入越南戰爭而關閉校園,古爾德當時還只是哈佛大學的助理教授,冒著不能升為永久教授(往往被不恰當地譯為「終身教授」)的危險參加了學生的抗議活動。他還擔任紐約馬克思主義組織布萊奇論壇和刊物《重思馬克思主義》的顧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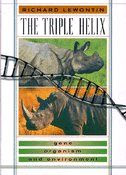
列萬廷著作:基因、生物體和環境
( The Triple Helix: Gene, Organism, and Environment )
( The Triple Helix: Gene, Organism, and Environment )
美國生物學界另一位更為公開的馬克思主義者、首創用生物化學方法研究遺傳多樣性的著名遺傳學家列萬廷(R.
Lewontin)是古爾德的同事和戰友,兩人合寫過多篇文章,特別是聯手批評新興的社會生物學。在20世紀70年代,列萬廷為抗議美國科學院屬下的全國科學委員會捲入越南戰爭,辭去院士一職,組織了一個名為「科學為人民
」的團體,古爾德是該團體的成員。
百科全書式的大師
百科全書式的大師
《科學》雜誌在死者略傳中稱,古爾德是極少數可以不臉紅地被稱為「文藝復興人物」的科學知識分子之一,這指的是他文理雙全,博學多才,是真正的百科全書式的大師。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另兩位百科全書式的大生物學家貝爾納(J.D. Bernal,1901-1971)和荷爾登(J.S.B. Haldane,又譯做霍爾丹,1892-1964)也都是馬克思主義者。這兩人都是英國人。貝爾納是分子生物學的先驅,首創用晶體衍射研究蛋白質結構,他的兩個學生佩魯茨(M. Perutz)和霍奇金(D.C. Hodgkin)因此分別於1962年和1964年獲得諾貝爾獎。他在1939年出版《科學的社會功能》一書,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地分析科學哲學問題,因此也被認為是科學哲學的創建者之一。他積極組織政治活動,被稱為「劍橋的聖人」,在其周圍聚集了一批左翼科學家。
有趣的是,貝爾納同時在蘇聯和美國獲得最高榮譽:前蘇聯授予他列寧獎章,美國授予他自由獎章。荷爾登是群體遺傳學的創建者之一,對生理學、遺傳學、進化生物學和生物化學都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同時又是多產的作家,發表過多部科普和文學著作,至今風行不衰,其名言常常在生物學家撰寫的隨筆中出現。荷爾登也熱衷於政治辯論,並在 1957年為抗議英國政府對蘇伊士運河的不公正處理而放棄英國國籍移民印度。此外,20世紀上半葉最傑出的遺傳學家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穆勒(H.J. Muller)也以思想左傾著稱,30年代因此被迫離開美國去歐洲,曾應邀去前蘇聯工作3年,後因不滿李森科主義而回到美國。
自覺地運用辯證法
在西方物理學家中,似乎沒有類似的重量級人物信仰馬克思主義。畢竟,生物學與人類社會的關係要比物理學密切得多,而生命現象的極度複雜也會促使研究者思考哲學問題。在面對複雜的生命系統時,強調全面、動態地看問題的辯證法不失為一種吸引人的分析工具。
 列萬廷和查德・萊維斯合著的書:
列萬廷和查德・萊維斯合著的書:《辯証的生物學家》
古爾德寫道:「當作為一種變化哲學的指南,而不是強制的教條戒律時,辯證法的經典法則體現了一種整體論的觀點,其看法隨著完整系統的各組分之間的相互作用而發生變化,並且將各組分自身當作同時是系統的產物和放入物。西方學者應該更認真地對待辯證思維,不應該因為某些第二世界國家(指前蘇聯及其盟國)製造了一個紙板式的版本作為官方教義,就因此拋棄它。」
列萬廷的生物哲學著作更自覺和明顯地運用了他們心目中的「辯證法」,他對基因、生物體和環境三者之間的關係的論述,是我見到的最深刻、獨到的分析,雖然他小心翼翼地避免用「辯證的」一詞,而改以「動態的」代之,雖然沒有一處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語錄,卻顯然是在運用辯證法思維。比古爾德更糟糕的是,列萬廷這些著作在美國學術界廣為人知,而在中國卻幾乎無人知曉。
一個時代即將結束
像古爾德、列萬廷這些信仰馬克思主義的西方學者,主要以大學為基地,被稱為學院左派。但是與其他學院左派不同,他們雖然也重視社會意識對科學研究的影響,卻不把科學研究完全當成「社會建構」而陷入相對主義的泥潭。他們更不敵視科學,屬於極少數不僅對科學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而且致力於溝通科學和人文、科學和公眾的左翼科學家。在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科學觀普遍走向與科學為敵的今天,他們更顯得難能可貴。
現在,古爾德走了,列萬廷也垂垂老矣(今年73歲),一個時代即將結束,抗拒西方學術界中反科學思潮的重任,反而要由他們的論敵威爾遜(E.O. Wilson,社會生物學的創建者)、道金斯(R. Dawkins,《自私的基因》的作者)等人一肩挑了。
---- 凡署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集者的立場 ----
《系列‧中國》chinaseries.blogspot.com
《grito de batalla》gritodebatalla.blogspot.com
《踐行者教育》activistseducation.blogspot.com
《再望‧古巴》cubahasta.blogspot.com
《這地球‧這世界‧這制度》planetworldsystem.blogspot.com
Reply all
Reply to author
Forward
0 new messages







